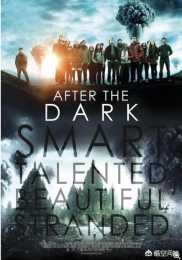編者按:這是一篇由慧田君約稿,哲友顧小北執筆的文章;轉載者請註明來自微信第一原創哲學公眾號「philosophs」。
在伊甸園東面的一個曠野裡,有一頭雄性怪獸貝西莫斯(Behemoth),另一隻母獸盤踞大海,名曰利維坦,他們在神創世紀的第六天出現,並將隨世界末日的到來而被作為奉獻給聖潔者的祭牲而消逝。
這個利維坦,強到足以與撒旦相提並論,她有另外一個名字,是為“七宗罪”裡的“嫉妒”(jealous)。
此說在不同的神話裡幻化成別的名字或性別,但無一例外的都把它描述成強有力的半神半獸的怪。
在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論者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的筆下,“利維坦”被用來指代一個能讓人們產生歸屬感的龐然大物——政府。
人啊,總是想要一個英雄來保護他們,美國有馬龍白蘭度,有喬治華盛頓、林肯、羅斯福,英國也有英國超人,有莎士比亞、簡·奧斯丁、狄更斯和白金漢侯爵,法國有理查曼大帝、路易十四、拿破崙,還有偉大的齊祖,中國英雄?
恕在下無能,還沒找到能被稱作“英雄”的人物。但是如“英雄”一般的存在卻與西方國家齊頭並進,為了抵禦各種外來的風險,求的一絲生機,人們自己創造了一個“利維坦”——政府,並使其機構不斷龐大細化,三省六部中央集權,馬其頓帝制,共和立憲各領風騷。
但政府這個“利維坦”正如她被上帝創造出來的初始使命一樣有雙面的性格。這個象徵強權的東西,由人組成,也由人來運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種半神半獸的品質,它在保護人的同時,又在吃人。
在《利維坦》成書的最後,霍布斯憂愁憂思喟嘆:「人類社會的最高理想就是把利維坦關進籠子裡」。
上帝這個慈眉善目又教人心生恐懼的存在張開雙手,似是無奈:“英雄在保護你們的同時,也會欺壓你們,吃你們”。
偏有一個人,他出生在霍布斯150年後的法國,與哲學先驅霍布斯一樣,他認為:
既然英雄的存在是一個無法逆轉的事實,那麼反抗與享樂理所當然的成為了生活的主流,成為活著的全部意義
。
在他的心目中,從功利主義裡脫胎出來的享樂主義(hedonism)以快樂為目標,成為了天生的最高的善。
他的名字叫薩德,薩德侯爵,全名當拿迪安·阿爾風斯·法蘭高斯·迪·薩德 (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Marquis de Sade)1740年6月2日出生於巴黎,1814年12月2日逝世於巴黎附近) 是一位法國貴族和一系列色情和哲學書籍的作者。
我們首先認識他,是從視覺衝擊開始,從他混亂的生活開始:
1763年,他與瑞內·佩拉吉·德·孟特瑞爾(Renée Pélagie deMontreuil)結婚。
1764年,父親死後,他繼承了他父親的與瑞士交界的三個省的榮譽總督的職務。
自此,薩德開始了他醜聞昭著的生活,他的生活遠遠跳出了當時法國貴族的放蕩主義所容許的範圍。
他多次虐待非常年輕的妓女和他家裡的男女傭人,後來與他的妻子一起虐待家裡的傭人。
他鞭打一個叫羅希·凱勒的女人並因此被捕。
他用糖摻雜麻醉品藥倒馬賽的妓女並強迫她們進行群交和雞姦。
他成為被告並被缺席判處死刑。
他逃往義大利。
後來,他在出逃時又拐騙了他的一個做修女的妯娌。
他的的妻子家裡也與他斷裂了。
他的丈母孃獲得了一個國王通緝令。
他返回巴黎時被捕並被關押。
他越獄未遂後被關押到巴士底獄,他在這裡被關押了五年半。
他在1789年某一天,向外面示威的人叫:“他們在這裡面殺被關的人!”可能他的這些叫喊導致了巴黎公眾攻佔巴士底獄。
他在法國大革命中被釋放。
他參加了極端的雅各賓派,宣揚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理想。
他拒絕交出他的家庭在普羅旺斯的宮殿和家庭財產。
他逐漸脫離了當時的政治主流,再次被捕並被判死刑。
他在1794年7月28日逃脫了斷頭臺,並在三個月後被釋放。
他窮途潦倒,不得不出賣他的家庭所有,幹雜活,他寫的作品賣不出多少錢。
他在拿破崙上臺後,因為寫了《於斯丁娜》和《於麗埃特》未經審判被關押。
他被稱瘋狂再次被關入瘋人院。
他在瘋人院完成了他的自傳式小說《閨房哲學》、《薩克森王妃布倫瑞克的阿德萊德》和《巴伐利亞的伊莎貝拉秘史》。
他還組織瘋人院裡的瘋人演了好幾齣戲。
他1814年逝於瘋人院內,享年74歲。
足夠香豔刺激足夠顛沛流離的生活,讓人不禁想起中國作家餘華筆下的福貴,同樣在年輕時候放蕩敗壞、紈絝糜爛(
福貴騎著“春風院”胖妓女去逛街,每次他經過丈人米店門口都要揪住妓女的頭髮,讓她停下,脫帽向丈人行禮:近來無恙?
),同樣經歷了物質的飽和到潦倒的過程,同樣是慢慢輸掉了自己的人生,同樣經歷黑暗時期和各種政治事件的折磨,卻也同樣能夠幻化為飽經憂患後的超然與達觀。
所不同的是,福貴知命,而薩德侯爵永遠保持激情。
年輕時候的浪蕩,成了他寫作與思考的源泉,多次入獄,反倒成了他寫作上最有成就的時間。他在巴士底獄內可以隨便借書、買書和讀書。
由於他的作品從哲學和性情上都非常與世俗格格不入,因此他多是偷偷地在小紙片上寫,並且,為了節約紙張不被別人發現他寫的字非常小。
薩德的創作從1769年開始,他一開始的業餘創作都是些遊記。入獄後他開始加強他的寫作。1782年他寫了《一個牧師和一個臨死的人的對話》(Dialogue entre un prêtre et un moribond 1782)。
在這篇作品中,已經漸漸顯露出他卓絕的思維能力以及對人性的探索,那個臨死的自由主義者能夠說服牧師虔誠的生活是無意義的,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的開篇所言:
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一個理想的社會,建立於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係。
薩德的未完成的小說《索多瑪的120天》(又名《放縱學校》)可謂極盡所能,描寫了120天暴亂的性生活,其中包括各種對被一群權貴綁架和奴役的男女青年的性行為。(
慧田哲學注:書裡大量的情色描寫足夠你燃燒,希望你能把握節奏
)這部作品1904年才被發現,直到1909年才發表。
由於書中大量性虐待情節,薩德被認為是變態文學的創始者,後與同以形同被虐心理著稱的奧國作家馬索赫齊名,薩德主義(Sadism)與馬索赫主義(Masochism)合稱為“SM”,即是現今“性虐待”的代名詞。
有讀者常常誤以為薩德在獄中即過著如小說裡一樣糜爛到足以瞠目的性虐生活,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那是在一個巴士底獄幽閉的空間裡,薩德避開眾目寫在小紙條上,涉及封閉、道德無涉的只為作者本人而存在的自洽世界。
它意在解構人與群體的微妙關係,一個理想的共建群體,一個建立於人與人之間而非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關係的群體;它傳達的是經由恐怖傳達的快感,經由壓迫而獲得的自由。
人們常常存在的恐懼,必然要以某種事物為物件,並歸之於某一種不可見的力量,諸神,上帝,不就是經由人類的恐懼創造出來的麼?
我以為,薩德侯爵想要傳達的一定不僅僅是讓人稍感不適的性,而是對某一種力量的反抗,集體無意識之下,人類的行為常常荒誕詭譎(
無數次隱秘暴虐的政治事件早就傳達了這一點,坑殺、細菌實驗、屠城、文化革命,無一不掠其極
)。
要知道,薩德侯爵可不僅僅是作家,他還是當時推翻政府統治的雅各賓派的積極分子。
有一幅畫叫《馬拉之死》,諸位一定不會陌生。畫面上,馬拉被刺殺在浴缸裡。匕首拋在地上,鮮血從馬拉的胸口流出,他的左手仍握著便箋,臉上露出憤怒而痛苦的表情。構圖的光影馬拉的身軀和麵部,具有紀念碑似的立體感。
馬拉,是雅各賓派的核心領導人,雅各賓派當政以後,他因為卓越的號召能力而成為該派的主席,但同時也是一個殘忍嗜血的活動家,往往不經審判便將政敵送上斷頭臺。
他患有嚴重的面板病,每天只有泡在灑過藥水的浴缸中才能緩解痛苦,於是,浴室就成了他最經常待著的辦公場所。
1793年7月11日,一位反對他的女士夏洛蒂藉口商談事宜,進入馬拉的浴室,並在他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行刺,結束了這位暴戾政客的生命。大衛的畫要表現的是暴政的消亡還是堅貞的正義感到現在都沒有定論。
想想吧,薩德並不單純,作為雅各賓派的激進分子,他要寫的不是性快感不是淫亂,而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一個烏托邦社會主義革命者對強權政治的反叛。
男人筆下的暴力美學總是與女性不一樣,它似乎總是關乎政治、關乎權力。那些致力於把“強者的權力”凌駕於人民之上,把物理力量和精神力量等量齊觀的,混淆社會、道德、理性這些概念,並把自然力量付諸王權的人或政府,都是薩德們反叛的物件。
男性與女性對待“性”的問題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作為一名女性讀者,倒是更願意看到越來越多的男性摒棄性別觀,將單純的力量化作對女性更多的關懷關心。
更長的歷史以來,女人在做愛時有高潮困難,女人能從陰蒂刺激或是自慰中更輕易地達到高潮,一直是個常識,在這裡不防分享一些個人的體驗,僅供參考。
就像你所能想象的那樣,熱情始終是所有肉慾中最美的部分,那是一種佔有和取得、攻掠和被攻掠,插入和被插入的慾望。不可否認的是,與親吻擁抱這些表達愛慾的動作一樣,這種慾望同樣存在於男人之間,女人之間。
因此,想要屬於對方,想要相處在一起、彼此交融的慾望,就是熱情。愛情之中,有部分是純然的生理感受,即想要共同達到高潮快感。
還有一部分,交給相擁入眠,呼吸對方的氣息,不但胸膛緊靠在一起,心靈亦是如此。聞著對方的體味,用你的舌撫弄他(她)的口唇,彷彿是自己的口唇一般,辨識他(她)的性器官的味道和觸感,用手深入探索它,並愛撫它。
在這個過程裡,達成愛的交談和諒解,彼此依偎,傳達身體最深的交融。做愛是什麼?重點不在機械的做,而是,對所愛之人的身體的記憶比其他任何記憶都更為持久。即便有時候,它已經在道德準繩之外。
當然,我也有理由相信,男人,在不能超越雙重標準的前提下,無論有多少性經驗,大部分男人仍覺得熱心中悵然若失,好像總是有那麼一點不滿足。這與女人開啟衣櫥的惆悵大概是一樣的吧。物化自己之後,可愛又愚蠢的人類啊,說什麼好呢?
所以,“仁慈的”薩德始終堅信不論多麼不道德的行為在世界上肯定有什麼地方會被自然容忍或甚至被贊成。就像霍布斯的“利維坦”,她被上帝創造出來,又被上帝利用制約人類。
那麼,對於每個人體內的“薩德”,對於“利維坦”這個龐大機器的建立,不過是恰好有助於人類“認識你自己”,不過是來自對內心的關照。
薩德作品中的色情部分寫得非常細膩,非常有幻想力,但許多性行為也很難想象可以做得到,他尤其擅長描寫與暴力和疼痛相連的行為,後來被人們稱為“薩德主義”的內涵。
他的文章也始終受到檢察和封禁的威脅。比如1963年德國將他的《閨房哲學》列入“威脅青少年的作品”中。
《閨房哲學》,也是薩德最有名的作品之一,可以說是薩德的自傳。在這本書裡他描寫了一個下午和此後的晚上一個貴族年輕淑女的性生活和哲學的啟蒙。其教師是一個女貴族,兩個男貴族和一個粗壯的農民。
在必需的恢復休息的時間裡這四個主角探討哲學問題。其中尤其同性戀的、享樂主義的、無神論的道爾曼色成為“不道德的教師”和薩德的替身。道爾曼色的哲學主題主要來自強人論。
薩德將這個理論理解為社會和精神的優秀者——即高等貴族——不顧一切地追求快樂的權利。
不顧一切地追求快樂,不就是“伊壁鳩魯主義”?
作為一名哲學愛好者,常常會有意識的對名詞概念產生濃厚興趣(權當做是初學者的執念吧),比如“伊壁鳩魯”。
伊壁鳩魯的倫理學概念強調,在我們考量一個行動是否有趣時,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它所帶來的副作用,即在追求短暫快樂的同時,也必須考慮是否可能獲得更大、更持久、更強烈的快樂。
從這一點上說,它可以當作弗洛伊德在本我(ID)快樂原則上的基礎,舉個例子,什麼叫“伊壁鳩魯主義”:
比如大街上看見一漂亮妞兒,本我(ID)說:哇!好漂亮哦,扣人心絃!令人心魄盪漾!我一定要勾搭勾搭?
超我(Superego)趕緊打了自己一巴掌:你怎麼這麼骯髒!不許這樣!
自我(Ego)又辯解道:哎~~不要吵了!這樣吧,必要的社會交往是可以的嘛!上前搭搭腔也是可以的嘛!!
伊壁鳩魯就是那個充當自我角色的小可愛。畢竟,老蘇說過: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沒有思維參與,僅靠下半身的勾搭也是不靠譜和無趣味的。
伊壁鳩魯還有一層解釋,即當對飢餓滿足在進行的時候,它就是一種動態的快樂,但是當飢餓已經滿足之後而出現的那種寂靜狀態就是一種靜態的快樂。
伊壁鳩魯認為追求第二種更為審慎一些,因為它沒有摻雜別的東西,而且也不必依靠痛苦的存在作為對願望的一種刺激。
薩德承襲了伊壁鳩魯的快樂原則,但又不同意性愛作為“動態”的快樂之一要被禁止,薩德認為性愛是被允許的,伊壁鳩魯的倫理學在別人看來是粗鄙的並缺乏道德的崇高性,但薩德,足夠真誠!他在獄外生活中,在小說裡構建了一個讓人瞠目的“理想世界”。
如果說《利維坦》是霍布斯的《上帝之城》,同時也是他的《懺悔錄》,那麼《閨房哲學》就是薩德的《理想國》,也是他的《瓦爾登湖》。
像是海德格爾發現了荷爾德林一樣,極具爭議的死亡模仿藝術家導演皮爾·保羅·帕索里尼發現了薩德作品除卻性以外的意義。
他將小說《索多瑪120天》的情節由瑞士搬到了二戰後期臭名昭著的薩羅共和國(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堡壘)。
電影的段落構成借用了但丁的《神曲》,分為“地獄之門”、“變態地獄”、“糞尿地獄”和“血的地獄”四章,極盡變態之能事。
一個身著白色皮大衣的貴婦,在廳堂中央,在鋼琴演奏裡講述。
“比雞姦更恐怖的是屠殺”。
“我們的英雄不僅熟悉尼采也熟悉胡伊斯曼斯。”
“一個有理性的人不會滿足殺同樣一個人,他會盡量去殺人。”
“爸爸的言語就是同情,孩子的,就是獻身。”
“小鳥在合唱,樹枝上充滿和諧。”
……
人的命運始終被一隻無形的手掌控著,拍完這部電影,帕索尼裡死在了萬聖節和萬靈節之間的夜晚,如同聖埃克蘇佩裡寫完《小王子》後死在了沙漠裡一樣極具戲劇性。
有人說他的死是有計劃的政治暗殺,也有人哀嘆這是一場藝術的殉難,是文化的儀式,但不管怎樣,戲劇化的生活現實讓這部同名電影及導演更加神秘隱蔽,這個只為他們本人而存在的自洽世界,這個極具視覺衝擊而給人的不適感的電影,成為位居十大禁片之首的邪典之作。
影片的最後,彈鋼琴的女孩兒從窗戶上翩然跳下。集中營裡充斥著暴怒、鞭笞、瘋狂、絕望以及屠殺,影片最後,在兩個男孩兒的舞蹈裡收束。整部片子你看到的是性還是政治,或者,是無法言語達及的對人類的失望,我也只能說你去看看就好了。
哲學從來都不為希臘人而興起,也不為那些從來沒有和平共和國的其他西方人而興起,而是在他們彼此有同等的恐懼的時候而興起的。
對兩性的恐懼,對時間的恐懼,對英雄及偉人的恐懼,都伴隨依賴,哲學曾經很長一段時間被當作人抵禦恐懼的東西,現在,它似乎更是一種依賴,熱愛它並且去接觸,從一個一個名詞開始,當它可是不那麼冷漠,不那麼不可接近,當它與你的生活相關聯,與你的愛人相關聯,它會變得更有趣味,更美麗一些。
當我們把薩德關進巴士底獄,“薩德”在我們體內。他用王爾德般的輕浮告訴我:“惡,莫大於輕浮。”
每個人都不應後悔曾經為享樂而活過,但卻永遠不能指望止於享樂。
我是曾經輕浮卻愛上水手的塞壬,你是利維坦麼?還是貝西莫斯?
今日「慧田哲學人公號」推送的題圖為:「諾曼底戰場」。今天(6月6日)是諾曼底登陸72週年。1944年的今天,三百萬士兵穿過英吉利海峽,登陸法國的諾曼底,在歐洲西線戰場的奧克角發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海上攻勢。現在我們鳥瞰這裡的戰壕、隧道以及炮火發射地中的每一個角落,都能感受到當年那蕩氣迴腸的氣息。
推薦閱讀:
薩德:狂暴就是對規範的僭越
Via:慧田君編|有異議請私信其微信「cc2cc-net」